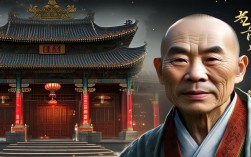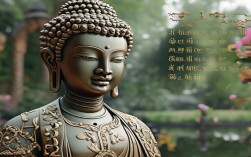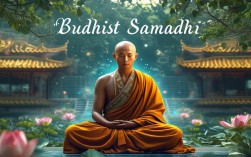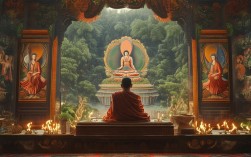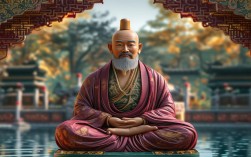周末去城郊的古寺本是为求一份心安,却未曾想撞见了生命中最具冲击力的“无常”,那日天色微阴,寺前的银杏叶刚落了满地,踩上去沙沙作响,像极了岁月低语,香炉里的青烟袅袅升起,混着檀香与柏木的气息,将整座寺庙裹在一种宁静又略带肃穆的氛围里,我沿着中轴线慢慢走,大雄宝殿的飞檐在灰蒙蒙的天幕下划出柔和的弧线,几个穿灰袍的僧人低眉走过,袂角带风,步履轻缓,仿佛踏着无形的经文。

刚转到后院的藏经楼,忽闻前方传来一阵急促的钟声——不同于平日里悠扬的禅钟,那声音短促、沉重,像一块巨石投入深潭,在寺庙的各个角落激起回响,我心里咯噔一下,正疑惑间,看见两个年轻僧人从客堂快步跑出,脸色凝重,低声说着什么,路过客堂时,我瞥见门边新贴了一张素白的讣告,墨迹未干:“某寺方丈上明下下老和尚,于癸卯年十月十五午时,安详示寂,世寿八十有二。”
“示寂”二字像针一样扎进心里,我昨天还看见老方丈在禅房前给几个孩子讲《心经》,声音虽沙哑,却带着让人心安的温和,他枯瘦的手指轻轻点着经文,眼睛里闪着光,怎么就“示寂”了?周围信众开始聚拢,有人低声啜泣,有人合掌闭目,有人茫然地看着讣告,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,我站在原地,看着那几张素纸被风吹得轻轻颤动,忽然想起《金刚经》里“一切有为法,如梦幻泡影,如露亦如电”的话,此刻才明白,那些曾经觉得遥远的“无常”,原来就在一呼一吸之间。
寺里的气氛很快从宁静转为肃穆,僧人们开始布置灵堂,藏经楼前的空地被临时辟出来,供桌上迅速摆上了方丈的黑白遗像、新鲜的白菊、青瓷净瓶,还有一盏长明灯,火苗在微风中摇曳,却始终不灭,有老居士说,老方丈圆寂前三天,还在修改寺院的修缮方案,说自己“要把庙里的漏雨屋顶修好,再走”;也有沙弥说,方丈圆寂那日清晨,还坚持早课,诵经声如往常般清晰,只是在结束时,轻轻说了一句“因缘已了,各自珍重”。
我站在人群外围,看着灵堂前缓缓跪下的僧人,他们双手合十,额头触地,肩膀微微颤抖,却始终没有发出哭声,这种沉默的悲伤比任何哀嚎都更具穿透力,像潮水一样漫过我的心头,忽然想起自己来寺庙的初衷——为工作焦虑,为未来迷茫,想求一个“确定”的结果,可此刻看着方丈的遗像,他嘴角带着一丝浅浅的笑意,仿佛只是睡着了,又仿佛在说:“别怕,一切都会过去。”

下午,寺里为信众安排了集体悼念,大家跟着僧人诵《阿弥陀经》,木鱼声与梵呗声交织,在古老的殿宇间回荡,我合掌站在人群中,听着“其国众生,无有众苦,但受诸乐”的经文,忽然不再感到恐惧,或许,方丈的圆寂不是结束,而是另一种形式的“解脱”——他离开了这个充满烦恼的娑婆世界,去往了没有痛苦的彼岸,而我们这些留在世间的人,所能做的,不是沉溺于悲伤,而是带着他的嘱托,好好活着,像他那样,在无常中保持慈悲,在平凡中践行道心。
离开寺庙时,天已放晴,夕阳的金光洒在银杏叶上,那些落叶不再显得凄凉,反而像镀了一层暖边,寺门口的银杏树下,有个小沙弥在扫地,他动作很轻,生怕惊扰了地上的落叶,我走过去,他抬头对我笑了笑,眼睛亮晶晶的,像方丈当年一样,那一刻,我忽然明白,真正的“永恒”从来不是肉身的永存,而是精神的传承,方丈虽然圆寂了,但他讲过的经、帮助过的人、传递的善意,都留在了这片寺庙里,留在了每一个见过他、听过他的人心里。
或许,这就是“无常”的意义——它让我们懂得珍惜,学会放下,明白生命的每一刻都值得认真对待,就像那盏长明灯,火苗会随风摇曳,却永远不会熄灭,因为点燃它的,是超越生死的慈悲与智慧。
以下是相关问答FAQs:

问:在寺庙遇到方丈圆寂,作为普通人应该怎么做?
答:遇到这种情况,首先应保持肃静,不喧哗、不围观,尊重逝者与僧众,可跟随寺内义工或僧人的指引,在指定区域静默合掌,或随缘参与集体悼念(如诵经、上香等),若情绪激动,可先到寺庙外围稍作平复,避免影响寺内秩序,拍照、录像是大忌,不仅打扰僧众,更是对逝者的不敬,离开时可将香火钱投入功德箱,或以捐赠寺院的方式表达哀思,核心是心怀慈悲,言行得体。
问:佛教中“圆寂”和“死亡”有什么区别?
答:在佛教语境中,“死亡”是凡夫俗子的生命终结,指神识离开肉体,进入六道轮回,仍有生老病死之苦;而“圆寂”特指修行有成就者(如高僧大德)的示现,意为“德圆满、寂灭安乐”,即熄灭一切烦恼、超越生死轮回,达到“涅槃”的境界,方丈等高僧圆寂,是修行圆满的自然结果,被视为“解脱”,而非凡俗意义上的“死亡”,故信徒常以“往生”“示寂”等词表达尊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