班禅额尔德尼是藏传佛教格鲁派(黄教)两大活佛转世体系之一,与达赖喇嘛共同构成格鲁派的核心领导架构,青海作为安多藏区的中心,自古以来便是藏传佛教东传的重要枢纽,班禅额尔德尼与青海佛教的渊源深厚,不仅体现在宗教传承的紧密联系上,更反映在文化融合、社会稳定及国家统一等多个维度,本文将从历史渊源、宗教实践、文化融合及现代传承等方面,系统梳理班禅额尔德尼与青海佛教的互动关系。

班禅体系的历史渊源与青海的早期联结
班禅额尔德尼的转世体系始于明末清初的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(1570-1662年),作为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的上师,罗桑却吉坚赞在格鲁派发展中扮演了“导师”角色,其宗教威望不仅巩固了格鲁派在西藏的地位,也为后来“班禅额尔德尼”封号的诞生奠定了基础,青海在元代起便纳入中央王朝管辖,明末清初,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率部进入青海,支持格鲁派对抗地方势力,罗桑却吉坚赞与固始汗的合作,标志着班禅体系与青海蒙古部族的正式联结——固始汗在西藏建立格鲁派政权后,青海成为格鲁派向卫藏输送人力、物力的重要基地,而班禅则通过青海的蒙古信众扩大了宗教影响力。
1713年,康熙帝正式册封五世班禅罗桑益西为“班禅额尔德尼”(意为“睿智的光明佛”),确立了班禅作为达赖喇嘛之下、格鲁派第二大活佛的地位,这一册封不仅具有宗教意义,更强化了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的管理,而青海作为连接内地与西藏的“咽喉”,自然成为班禅体系与中央王朝互动的重要通道,清代,青海蒙古各旗(如和硕特、土尔扈特等)均奉班禅为宗教领袖,定期派遣使者前往日喀则扎什伦布寺请安,同时邀请班禅派高僧到青海弘法,这种双向互动使青海佛教与班禅体系形成了“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”的依存关系。
班禅在青海的宗教实践与寺院弘法
班禅额尔德尼与青海佛教的联结,最直接的体现是其历代转世在青海的宗教活动及对当地寺院的扶持,青海现有藏传佛教寺院400余座,其中格鲁派寺院占比超60%,塔尔寺、夏群寺、广惠寺等均与班禅体系有着深厚渊源。
(一)塔尔寺:格鲁派在青海的弘法中心
塔尔寺(藏语“衮本贤巴林”,意为“十万狮子吼佛弥勒洲”)位于青海西宁湟中县,是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诞生地,被誉为“黄教之源”,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曾明确表示:“塔尔寺乃宗喀巴大师根本道场,当以护持为己任。”在其推动下,塔尔寺逐步发展为集显密教学、辩经、艺术于一体的综合性寺院,17世纪中后期,五世班禅罗桑益西应青海蒙古王公之邀,驻锡塔尔寺三个月,期间为僧俗信众讲授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,并主持了“时轮金刚灌顶法会”,吸引来自青海、甘肃、四川的数万信众参与,极大提升了塔尔寺在安多藏区的宗教地位,此后,六世至十世班禅均曾派驻锡代表常驻塔尔寺,管理寺院事务、指导僧侣修行,塔尔寺的“显宗学院”“密宗学院”“时轮学院”等教学机构,至今仍沿用班禅时期确立的教材与学制。
(二)九世班禅与青海的深度互动
近代以来,九世班禅额尔德尼·曲吉尼玛(1883-1937年)与青海的关联尤为密切,1923年,因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政教权力分配上产生矛盾,九世班禅被迫离开西藏,辗转来到青海,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流亡弘法生涯,在青海期间,他先后驻锡西宁塔尔寺、玉树结古寺等地,足迹遍布海东、海南、黄南等藏区,1925年,九世班禅在西宁创建“青海番族文化促进会”,推动藏文教育与现代文化在青海的传播;1932年,他主持修复了玉树文成公主庙(藏语“嘎达那彭拉康”),将汉藏文化交融的历史遗迹纳入佛教保护体系,强化了青海作为“汉藏文化走廊”的地位,1937年,九世班禅在青海玉树圆寂,临终前留下“维护国家统一、促进民族团结”的遗训,其灵塔现供奉于塔尔寺“大金瓦殿”旁,成为信众缅怀的重要场所。
(三)寺院管理与僧侣培养
班禅额尔德尼对青海佛教的另一重要贡献,是建立了系统化的寺院管理制度与僧侣培养体系,清代以来,班禅通过向青海各大寺院派遣“堪布”(住持)或“经师”,规范寺院宗教活动,塔尔寺的“四大赛赤”(即大管家)中,有一席由扎什伦布寺直接委派;夏群寺的“显宗学院”教材,直接采用扎什伦布寺的“五部大论”讲义,在僧侣培养上,班禅体系强调“显密兼修”,要求僧侣先在塔尔寺等青海寺院完成显宗学习(因明学、般若学等),再赴扎什伦布寺深造密宗,这种“先安多后卫藏”的培养模式,既保证了青海佛教人才的质量,也强化了扎什伦布寺对安多藏区的宗教影响力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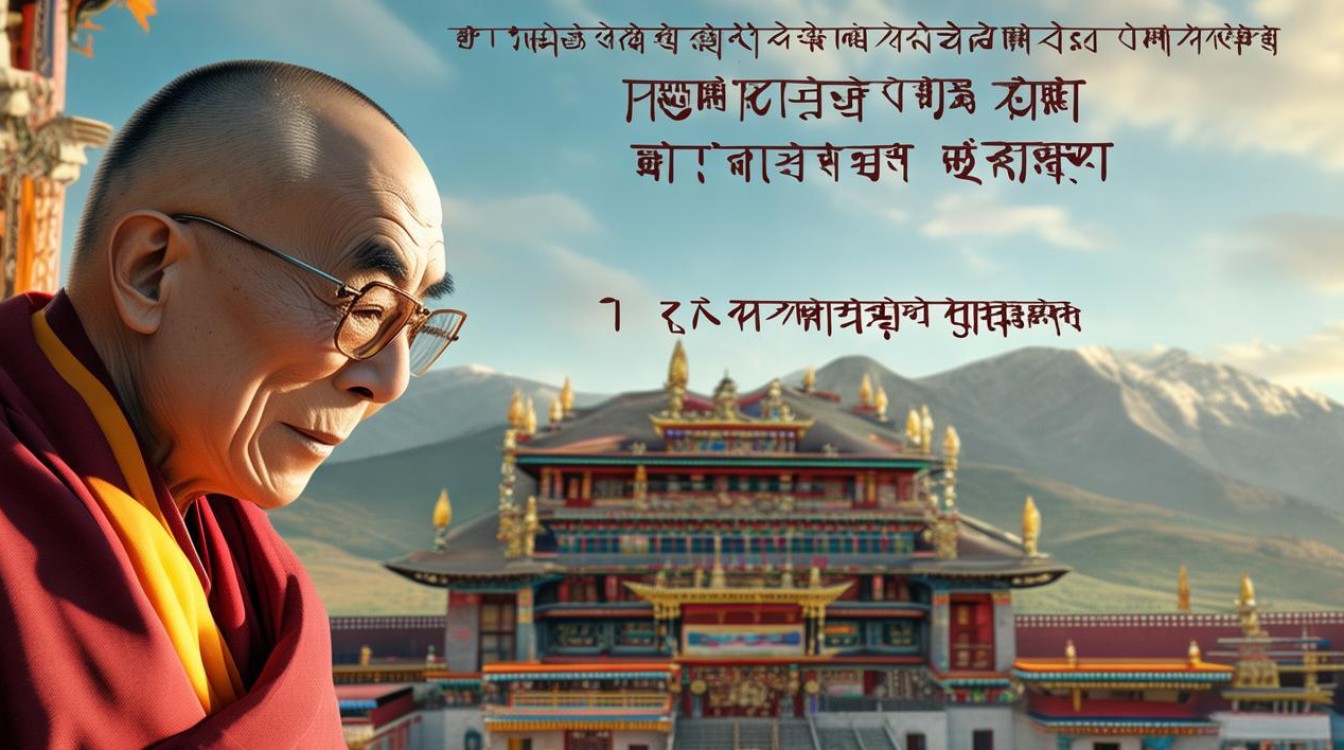
班禅与青海佛教的文化融合及社会影响
青海是多民族聚居区,藏、汉、蒙古、土、撒拉等民族长期共存,藏传佛教作为纽带,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交融,班禅额尔德尼在青海的弘法活动,始终以“文化互鉴、民族和谐”为宗旨,形成了独具特色的“青海佛教文化模式”。
(一)艺术与建筑的多元融合
班禅体系推动青海佛教艺术呈现出“藏汉蒙结合”的风格,以塔尔寺的“酥油花”为例,其制作技艺虽源于西藏,但在九世班禅指导下,融入了汉族的雕塑技法与蒙古族的色彩审美,形成了“人物写实、场景宏大”的独特流派;寺院的建筑风格也兼具藏式“碉楼”与汉式“歇山顶”特点,如塔尔寺“大经堂”的歇山顶屋檐、斗拱装饰,便是汉藏建筑艺术的融合之作,班禅还支持青海寺院用蒙文、汉文翻译佛经,如五世班禅曾组织高僧将《金刚经》译为蒙文,供青海蒙古族信众诵读,这种多语言佛经传播,打破了民族间的文化壁垒。
(二)社会稳定与国家认同
班禅额尔德尼始终将“护国利民”作为宗教实践的核心准则,清代,七世班禅丹白尼玛曾通过青海蒙古王公,向清廷呈献“丹书克”,表达对中央政权的拥护;民国时期,九世班禅在青海发表“拥护五族共和”通电,谴责分裂行径,号召藏区民众“同心同德,共建国家”;1951年,十世班禅额尔德尼·确吉坚赞(1938-1989年)派代表赴北京参与和平解放西藏谈判,并在青海发表讲话:“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班禅额尔德尼始终与中央政府同心同德。”这些行动不仅维护了国家统一,也强化了青海各民族对“中华民族共同体”的认同。
(三)慈善与教育的社会责任
班禅体系在青海积极践行“慈悲济世”的佛教理念,清代,四世班罗桑却吉坚赞曾从扎什伦布寺调拨银两,在青海湟源、贵德等地设立“粥厂”,救济贫困牧民;近代,九世班禅在青海创办“喇嘛医院”,为藏蒙牧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;十世班禅改革开放后视察青海,推动塔尔寺、夏群寺等寺院开办“佛学班”与“文化补习班”,既培养宗教人才,也提高僧侣的现代文化素养,这些举措使青海佛教不仅是宗教信仰的载体,更成为社会公益的重要力量。
现代班禅与青海佛教的传承发展
改革开放以来,在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指引下,青海佛教迎来新的发展机遇,班禅额尔德尼的宗教领袖地位进一步巩固,成为推动青海佛教健康传承的核心力量。
(一)宗教文化的保护与传承
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多次强调“宗教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”,在青海推动寺院“文物保护”与“教义阐释”并重,1980年代,他亲自参与塔尔寺“大金瓦殿”修复工程,要求“修旧如旧”,保留藏传佛教建筑的原真性;支持青海佛学院成立,将《宪法》《民族区域自治法》纳入僧侣课程,培养“政治上靠得住、宗教上有造诣”的宗教人才,2020年,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·确吉杰布在青海塔尔寺主持“时轮金刚法会”,来自青海、甘肃、四川的数万信众参与,法会通过互联网直播,实现了传统宗教与现代传播方式的结合。

(二)民族团结与生态保护
新时代,班禅额尔德尼继续发挥“桥梁纽带”作用,2019年,十一世班禅视察青海玉树,在文成公主庙呼吁“保护三江源生态,守护中华水塔”,并带领僧侣种植“班禅林”;2022年,他在西宁与各民族宗教代表座谈时指出:“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,共同守护民族团结、宗教和睦的大好局面。”这些活动使班禅成为青海民族团结的“精神象征”,也引导佛教界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。
班禅额尔德尼与青海佛教重要历史事件及影响表
| 时间 | 事件 | 影响 | |
|---|---|---|---|
| 1642年 | 四世班禅与固始汗合作 | 固始汗率蒙古军入藏,四世班禅支持其推翻噶玛政权,确立格鲁派统治地位 | 奠定格鲁派在藏区的统治基础,青海成为格鲁派向卫藏输送力量的重要基地 |
| 1713年 | 康熙册封五世班禅 | 康熙帝册封五世罗桑益西为“班禅额尔德尼”,确立班禅转世体系 | 提升班宗教地位,青海蒙古族、藏族对班禅的信仰进一步巩固 |
| 1923-1937年 | 九世班禅青海流亡弘法 | 因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失和,九世班禅辗转青海各地,在西宁、塔尔寺、玉树等地弘法 | 扩大班禅在青海及安多藏区的影响力,促进青海寺院建设与僧侣教育 |
| 1980年 | 十世班禅视察青海 | 十世班禅到塔尔寺、夏群寺视察,推动寺院修复与宗教政策落实 | 恢复青海佛教正常宗教活动,为寺院管理现代化奠定基础 |
| 2019年 | 十一世班禅玉树视察 | 在文成公主庙呼吁生态保护,带领僧侣种植“班禅林” | 引导佛教界参与生态文明建设,强化班禅在新时代的社会影响力 |
相关问答FAQs
问:班禅额尔德尼与达赖喇嘛在青海佛教中的地位有何异同?
答:班禅额尔德尼与达赖喇嘛同属藏传佛教格鲁派两大活佛体系,在青海佛教中均具有重要地位,相同点在于:二者均为格鲁派最高宗教领袖,其转世体系均得到中央政府册封,对青海藏传佛教的发展、寺院管理、僧侣培养等具有核心影响力,不同点在于:达赖喇嘛的传统驻锡地为拉萨布达拉宫,侧重于卫藏地区的宗教事务;而班禅额尔德尼的传统驻锡地为日喀则扎什伦布寺,因青海地处安多藏区与内地的交界地带,班禅在青海的弘法活动更侧重于连接藏区与内地,促进多民族文化交流,且历史上班禅与青海蒙古部族的关系更为密切,如在固始汗时期共同支持格鲁派发展。
问:青海有哪些与班禅额尔德尼密切相关的佛教寺院?它们有何特色?
答:青海有多座与班禅额尔德尼密切相关的佛教寺院,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塔尔寺和玉树结古寺,塔尔寺是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,位于青海西宁,被誉为“黄教之源”,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曾在此修行,五世班禅、十世班禅均曾到此讲经、主持法会,寺院的“酥油花”“壁画”“堆绣”被誉为“塔尔寺三绝”,融合了藏汉艺术风格,是班禅与青海佛教文化融合的体现,玉树结古寺则是九世班禅晚年驻锡和圆寂之地,1937年九世班禅在玉树圆寂后,寺院建有“班禅大师纪念塔”,成为青海信众缅怀班禅的重要场所,该寺以宁玛派与格鲁派融合为特色,体现了班禅在青海多民族、多教派地区促进宗教和谐的贡献,夏群寺、广惠寺等也曾迎来班禅驻锡,对寺院的宗教地位和文化传承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