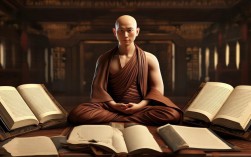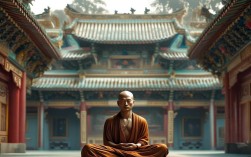玄奘,唐代著名高僧、佛经翻译家、旅行家,其一生与印度佛教紧密相连,公元627年,玄奘为求取佛教原典,纠正国内译本谬误,毅然从长安出发,踏上了西行求法之路,他穿越戈壁荒漠,翻越帕米尔高原,历经九死一生,最终抵达佛教发源地印度,开启了一段长达十余年的求法之旅,对中印佛教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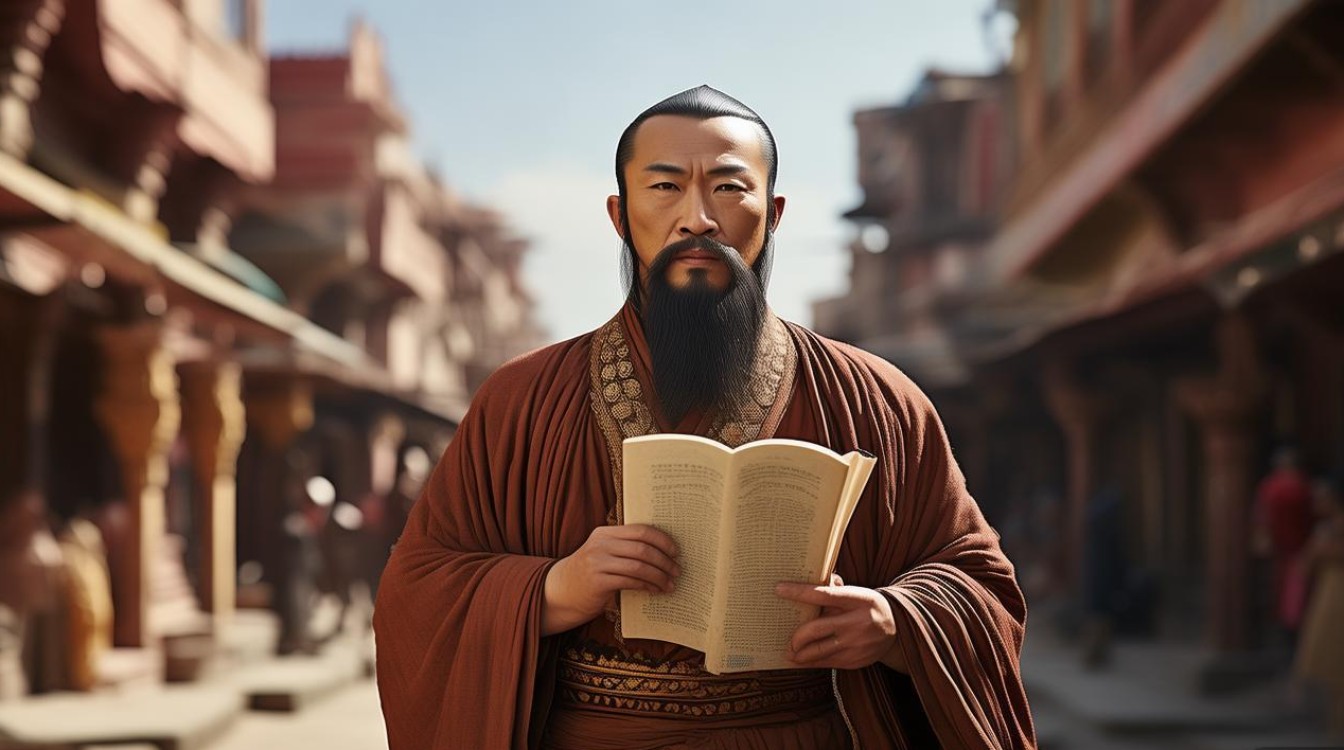
在印度,玄奘首先抵达北印度犍陀罗国,先后访问了佛陀圣地菩提伽耶、王舍城那烂陀寺等佛教中心,那烂陀寺是当时印度最高学府,他在此师从戒贤法师,学习《瑜伽师地论》《大般若经》等大乘佛教经典,深得戒贤法师赏识,被尊为“三藏法师”,玄奘在那烂陀寺学习了五年,不仅系统掌握了瑜伽行派的理论,还研习了因明学、声明学等五明,成为贯通大小乘、学识渊博的佛学大师,此后,他游历印度全境,足迹遍布今印度、尼泊尔、巴基斯坦等地,参访了上百座寺院,与高僧大德交流辨析,积累了丰富的佛学知识。
玄奘在印度的活动并非仅限于学习,还积极参与佛教辩论,公元642年,他应戒日王之邀,在曲女城主持无遮大会,与会者有印度十八国王、大小乘学者外道数千人,玄奘以所著《会宗论》《制恶见论》立论,任人问难,历时十八天无人能破,其博学与辩才震动印度,被大乘尊为“大乘天”,小乘尊为“解脱天”,成为印度佛教史上的一段佳话,戒日王为表彰其功绩,特建大乘佛寺,并邀其留在印度弘法,但玄奘因“本学在心,归诚佛所”,婉拒邀请,决意携带经像归国,将印度佛教精髓传播至中土。
公元645年,玄奘携657部梵本佛经及佛舍利、佛像等返回长安,唐太宗亲自接见,组织译场,开启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译经事业,玄奘的翻译以“直译”与“意译”结合,力求准确传达原典义理,共译出《大般若经》《瑜伽师地论》《成唯识论》等75部1335卷,占唐代译经半数以上,构建了汉传佛教唯识宗、法相宗的理论体系,其翻译不仅纠正了以往译本的讹误,更使印度大乘佛教思想得以系统传入中国,推动了中国佛教的义理化发展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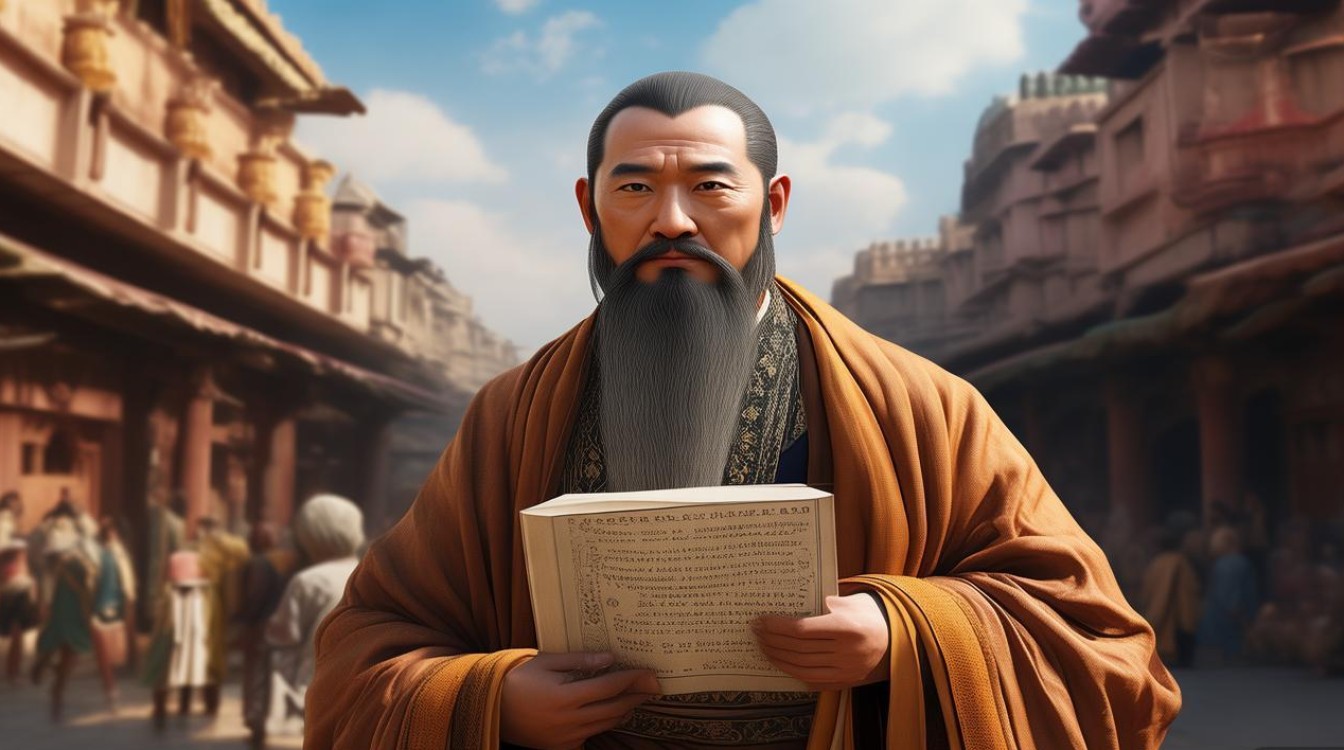
玄奘口述、辩机编撰的《大唐西域记》,详细记录了他亲身经历的110个及得之传闻的28个国家的山川地理、风土人情、宗教信仰,特别是对印度佛教圣地的描述,成为研究古代印度历史、文化、佛教的珍贵文献,19世纪以来,该书被译成多种文字,为印度考古学、历史学提供了重要依据,甚至帮助考古学家发掘出那烂陀寺遗址等古迹,堪称“中印文化交流的桥梁”。
玄奘西行求法,不仅是一位宗教信徒的修行之路,更是一次文明对话的壮举,他以毕生精力将印度佛教经典与思想引入中国,同时也将中华文化传播至印度,促进了两大文明的互鉴与融合,其精神与贡献,至今仍为世人所敬仰。
FAQs
Q1:玄奘在印度学习期间,为何选择那烂陀寺作为主要学习地?
A1:那烂陀寺是公元5至12世纪印度佛教的最高学府,由笈多王朝支持建立,藏书丰富,名师云集,尤其以戒贤法师主持的瑜伽行派教学体系最为权威,玄奘西行前听闻戒贤法师讲授《瑜伽师地论》未决之疑,故决心前往求法,那烂陀寺的学术氛围、师资力量和经典资源,使其成为玄奘系统学习大乘佛教义理的理想之地。

Q2:《大唐西域记》为何能成为研究古代印度的重要史料?
A2:《大唐西域记》是玄奘根据亲身游历见闻整理而成,内容涵盖印度各国的地理疆域、政治制度、经济生活、宗教习俗(尤其是佛教发展)、语言文字等,细节详实且客观中立,由于古代印度文献多已散佚,该书为后人提供了7世纪印度社会状况的第一手资料,例如对那烂陀寺、佛陀伽耶等圣地的描述,已被近代考古发掘证实,成为重构古代印度历史的关键文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