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遇恩师时,我正陷在人生的迷雾里,那时刚大学毕业,工作不顺,亲人病重,夜里常对着天花板发呆,觉得日子像被揉皱的纸,再也展不平,一个偶然的周末,我走进城郊的古寺,想找个地方静静,却在后院的菩提树下看见他:穿着洗得发白的灰布僧衣,蹲在地上捡落叶,枯枝一样的手指轻轻拂过草叶,嘴里念着“阿弥陀佛”,声音像山泉一样清,我站在原地,看着他捡完一片又一片,忽然觉得心里的褶皱被什么抚平了些。

后来常去寺里找他,他总在客堂待着,一张旧木桌,一壶粗茶,见我来就笑,眼睛弯成月牙:“坐,喝杯茶。”茶是寺里自己种的,入口微苦,回味却甘,他从不问我为何烦恼,只在我沉默时,说些看似平常的话,有次我抱怨工作难做,他指着桌上的青瓷碗:“你看这碗,有缺口吗?”我摇头,他说:“可它装过茶,也装过水,装过香灰,也装过雨水,人也是,别总盯着自己缺什么,想想自己装过什么。”那天阳光从窗棂漏进来,落在他袖口的补丁上,我突然明白,他说的不是道理,是活出来的智慧。
他讲经从不用经书上的套话,有次讲“无常”,他带我去看寺后的老梅树。“冬天开得最盛,春天就落了花,夏天结青果,秋天掉叶子,你说它无常,可它每年都开,你说它常住,可没有一朵花能留到明年。”风吹过,叶子簌簌落,他弯腰接住一片:“无常不是可怕,是提醒我们,每一刻都要好好活。”后来我遇到亲人离世,抱着他在客堂哭了一下午,他没说“别难过”,只递给我一块素饼:“吃吧,肚子空了,心更空。”那饼是寺里的义工做的,粗糙却暖,我咬一口,眼泪掉在饼上,他拍拍我的背:“生死像这饼,吃下去就融入你了,哭什么呢。”
他对每个人都一样,不管有钱没钱,有地位没地位,有个拾荒老人常来寺里讨饭,他总把自己的那份素菜拨一半给老人,还帮老人补衣服,有次老人走后,我说:“师父,您对他这么好,不怕他……”他打断我:“怕什么?他饿了,给口吃的;他冷了,给件衣服,佛说‘慈悲喜舍’,不是对好人,是对一切众生。”我看着他补衣服的手,针脚歪歪扭扭,却很密,突然想起他常说:“修行不是念多少经,是念多少人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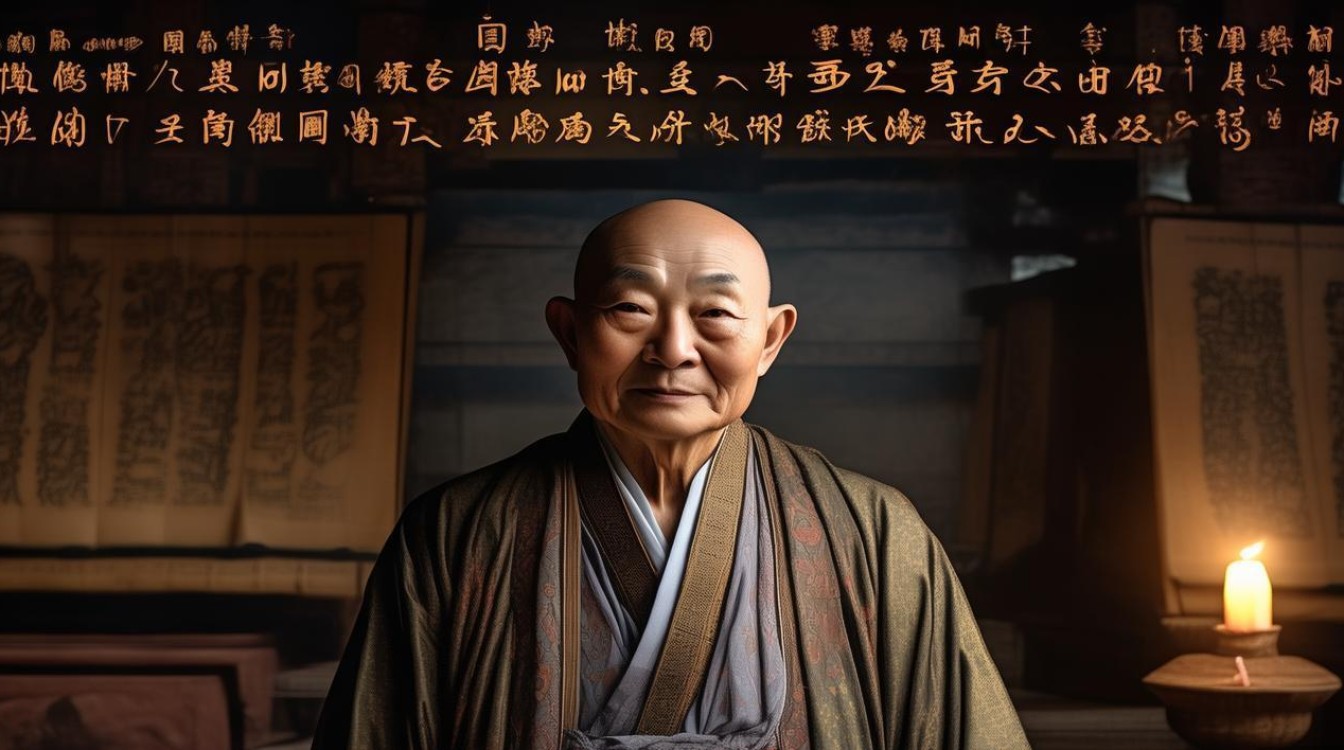
去年冬天,他圆寂了,那天我在外地出差,接到电话时,站在酒店窗前,看着外面的雪,忽然想起他说的“雪化了就是水,水冻了就是雪,人来了,人去了,都是这个理”,我没哭,只是给寺里打了电话,说想捐口棺材,住持说:“师父留了话,说火化后,骨灰撒在后山的梅树下,和那棵老梅树作伴。”我开车回去时,雪停了,阳光很好,路上想起他总说“阿弥陀佛”,不是“往生极乐”,是“感谢你来了”——感谢每个众生来度他,也感谢他能度每个众生。
现在遇到难处,我总想起他说的那碗茶,那棵梅树,那块素饼,他没教我念多少经,却让我学会了怎么活:不执着得失,不抱怨苦难,对世界温柔,对自己慈悲,有时候半夜醒来,仿佛还能听见他的声音,像山泉一样清,从很远的地方流过来,流到我心里,我想,这就是“难忘”吧——不是记得一个人,是记得他用生命告诉我的,怎么做一个温暖的人。
| 恩师的日常言行 | 对我的启示 | 我在生活中如何实践 |
|---|---|---|
| 蹲在地上捡落叶,念“阿弥陀佛” | 修行在细微处,不轻视任何小事 | 看到地上的垃圾会捡起,对服务人员说“谢谢” |
| 用青瓷碗比喻“装过什么” | 不执着于缺陷,珍惜经历 | 工作中遇到挫折,想“这碗又装了新东西” |
| 带我看老梅树讲“无常” | 接受变化,活在当下 | 亲人离世后,不再追问“为什么”,而是记得相处的温暖 |
| 给拾荒老人分素菜、补衣服 | 慈悲不分对象,平等对待 | 定期去敬老院做义工,给流浪猫喂食 |
FAQs
问:佛教恩师的“慈悲”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?
答:恩师的慈悲不是抽象的,而是融入在每一个细节里,他会蹲在地上捡落叶,因为“每片叶子都有生命”;他会把素菜分给拾荒老人,因为“众生平等”;他会在弟子痛苦时递一块素饼,因为“身体安了,心才安”,他的慈悲没有分别心,不因对方身份高低而不同,是“无缘大慈,同体大悲”的体现,这种慈悲让我明白,真正的善良不是刻意为之,而是把众生放在心里的自然流露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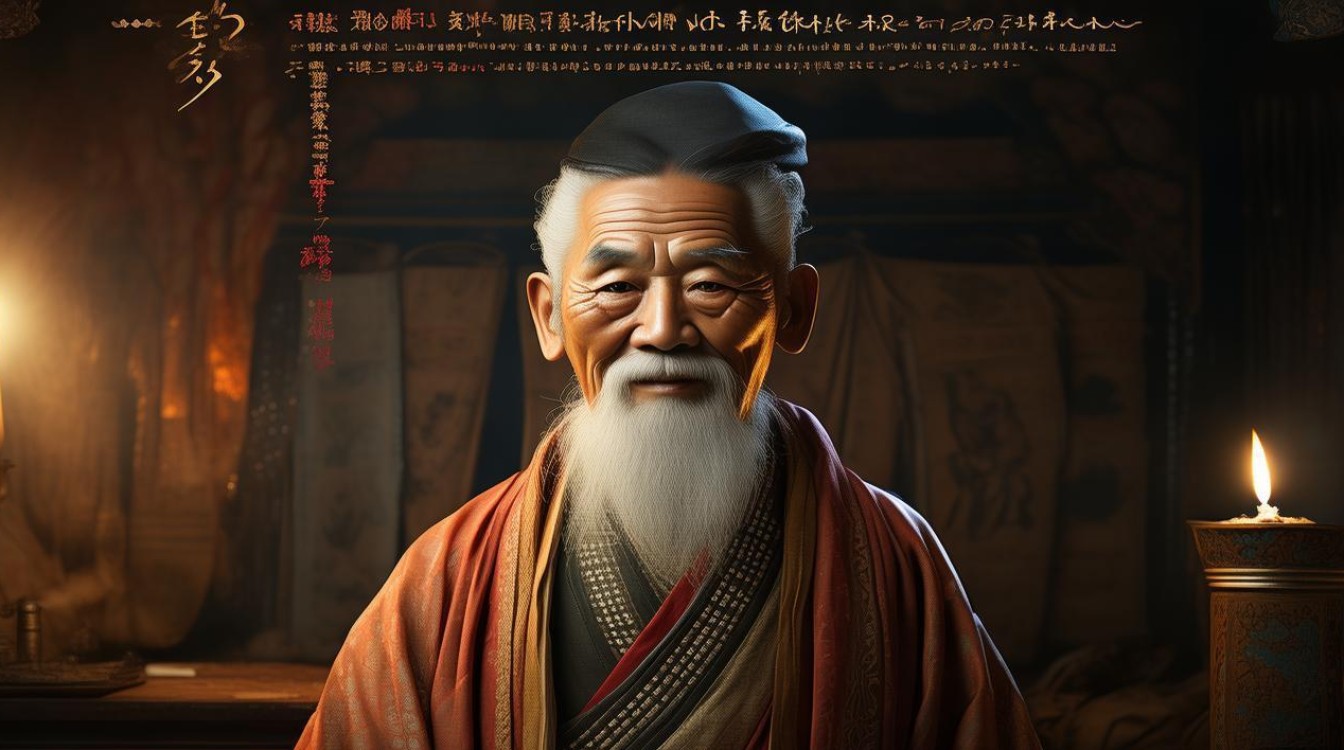
问:如果想念恩师,可以用什么方式纪念他?
答:恩师常说“最好的纪念是活出他的样子”,可以多做些符合他教诲的事:比如坚持行善,帮助需要帮助的人;比如在生活中践行“平常心”,遇到顺逆不执着;比如把他的智慧分享给身边的人,就像当年他耐心开导我一样,也可以去寺里种一棵树,或定期做义工,让这份慈悲传递下去,恩师说过“阿弥陀佛”是“感谢”,当我们带着他的教诲好好生活,就是对最好的纪念。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