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安法师在开示中常提及义净三藏法师,将其视为中国佛教史上“行解并重”的典范,尤其推崇其对戒律的坚守与求法实践的坚韧精神,义净法师(635-713)俗姓张,齐州(今山东济南)人,唐代高僧、旅行家、翻译家,与玄奘法师、法显法师并称为“三大求法高僧”,他的一生以“戒为津梁,法为舟楫”,不仅为中国佛教带来完整的律藏体系,更以亲身实践诠释了“佛法在世间”的真谛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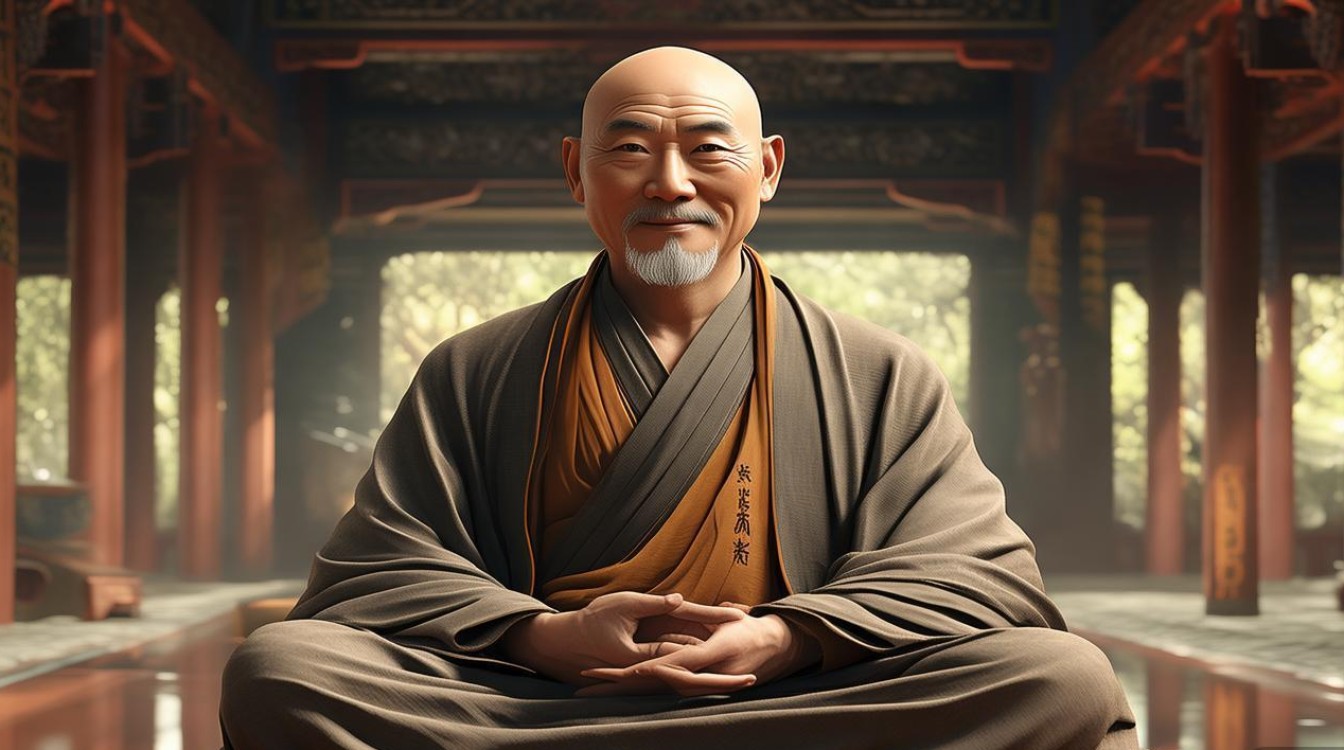
生平与西行:以生命求法的“弘法使者”
义净法师自幼出家,天性聪颖,少年时便对佛法义理有深刻领悟,他目睹初唐时期中国戒律传承的混乱——当时律典多属抄撮传译,戒本残缺,僧团持戒标准不一,遂生“西天求律”之志,咸亨二年(671年),37岁的义净从广州搭乘商船,经海路踏上西行求法之路,与法显、玄奘的陆路行进不同,他选择了更为艰险的海路:途中遭遇风暴,船漂至室利佛逝(今印尼苏门答腊岛),滞留半年后继续前行;后抵达印度,在那烂陀寺学习十年,师从高僧智月、达摩鞠多等,精研《根本说一切有部律》等律典,兼习中观、瑜伽行派学说。
游历印度三十余国后,他于证圣元年(695年)携带梵本经论400部、舍利300粒回到洛阳,受到武则天隆重迎接,此后,他组织译场,历时20余年译出经典56部、230卷,根本说一切有部律》多达150卷,填补了中国律藏的空白;他著述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》,以亲历视角记录南亚佛教戒仪、僧团生活及求法僧事迹,成为研究7世纪印度及东南亚历史的珍贵文献,大安法师指出,义净的西行不仅是“求法”,更是“传法”——他将印度律学的完整体系带回中国,推动了中国律宗的规范化发展,其“不为自己求安乐,但愿众生得离苦”的发心,正是大乘菩萨行的生动体现。
译经与著述:以戒律为“佛法命脉”的坚守
义净法师的弘法核心始终围绕“戒律”展开,大安法师强调:“戒是无上菩提本,长养一切诸善根。”在义净看来,戒律是佛法住世的根本,僧团的清净、修行的成就,皆以持戒为前提,当时中国佛教虽已传入四分律、十诵律等,但戒本传承不一,实践中多有混淆,义净远赴印度求取《根本说一切有部律》,该部律典体系完整、细节详尽,涵盖僧尼戒律、威仪制度、日常行事等,为僧团提供了明确的持戒依据。

他翻译的经典中,除律藏外,还有《金光明最胜王经》《大孔雀咒王经》等,金光明经》的译传,推动了“金光明忏法”的盛行,对汉传佛教忏法影响深远,而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则系统记录了印度僧团的“日用轨则”:如食不嚼杨枝、过午不食、衣法安陀会(袈裟搭制)等,不仅为当时中国僧团提供了戒仪参考,更揭示了“戒律并非刻板教条,而是调伏身心、护持道业的善巧”,大安法师特别指出,义净的著述“既有对戒义的深刻阐释,又有对戒行的细致实践”,他要求弟子“解在行中,行由解立”,反对脱离戒律的空谈玄理,这一思想对后世禅净融合的修行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大安法师的解读:行解并重的“现代启示”
大安法师在解读义净法师时,始终将其置于“末法时代”的背景下,强调其精神的现实意义,他认为,义净的“行”——即20余年的西行求法、20余年的译经弘法,是对“难行能行、难忍能忍”菩萨行的最好诠释;而其“解”——即对戒律义理的精准把握、对佛法契理契机的阐释,则为修行者指明了“以戒为基、以慧为导”的道路。
针对当代佛教存在的“重解轻行”“戒律松弛”等问题,大安法师以义净为榜样,提出“修行要从根本戒做起”,他指出,义净之所以能在异国他乡坚持求法,源于对“戒法住世”的坚定信念;之所以能在译经中保持严谨,源于对“法脉传承”的敬畏之心,这种“以法为命、以戒为师”的精神,正是当代佛教徒最需传承的,大安法师也提到,义净的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中“随方毗尼”的思想——即戒律的践行需结合不同地区的文化习俗,对处理“佛教中国化”与“戒律根本性”的关系具有重要启示:戒律的本质是“护心”,而非执着于形式,应在坚守根本原则的基础上,契理契机地适应时代需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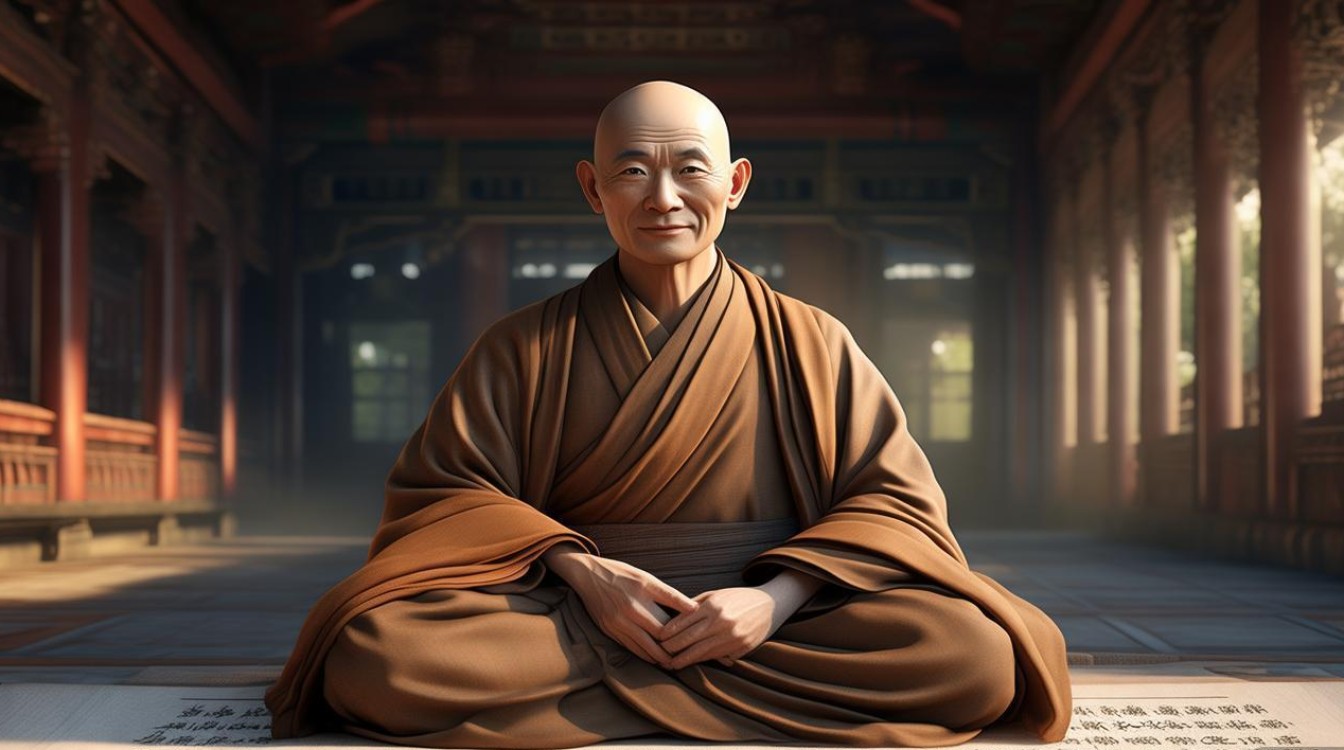
义净与法显、玄奘求法精神的对比(简表)
| 维度 | 法显法师 | 玄奘法师 | 义净法师 |
|---|---|---|---|
| 出行时间 | 东晋隆安三年(399年) | 唐贞观三年(629年) | 唐咸亨二年(671年) |
| 路线 | 陆路(丝绸之路南线) | 陆路(丝绸之路北线) | 海路(广州→室利佛逝→印度) |
| 核心贡献 | 带回律藏《摩诃僧祇律》,著《佛国记》 | 带回经论657部,译经75部,著《大唐西域记》 | 带回律藏400部,译经56部,著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 |
| 侧重领域 | 戒律(大乘戒与小乘戒并重) | 经论与唯识学 | 律藏根本说一切有部及戒仪实践 |
FAQs
问:义净三藏法师的西行与法显、玄奘相比,有哪些独特之处?
答:义净西行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:一是路线选择,他放弃陆路而取海路,虽风险更高,却开辟了中印海上交通的新通道;二是侧重领域,法显、玄奘以“经论”为主,义净则以“律藏”为核心,填补了中国佛教戒律体系的空白;三是著述视角,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不仅记录求法历程,更详述印度僧团的“日常戒仪”,为佛教实践提供了“操作手册”,这是前两者未曾涉及的层面。
问:大安法师为何特别推崇义净三藏法师的戒律思想?对现代修行者有何启示?
答:大安法师推崇义净的戒律思想,核心在于“行解并重”的实践精神,义净认为,戒律是“佛法寿命”,若无戒律,则“法不久住”;戒律需与智慧结合,不能执着于形式而忽视“调伏心性”的根本,对现代修行者而言,这一思想的启示在于:一要重视“根本戒”,明确修行的底线与原则;二要践行“生活戒”,将持戒融入日常,如过午不食、不妄语等,在细节中磨练心性;三要理解“开遮持护”,契理契机地践行戒律,避免“死守戒条而失慈悲”,正如义净所言,“宁持戒而死,不破戒而生”,这种对戒法的坚守,正是当代佛教护持正法、净化世间的根本。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