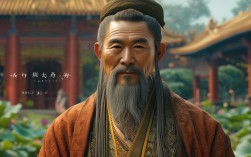圆瑛法师(1878—1953),近代中国佛教界的领袖人物,俗姓吴,名悟元,福建古田县人,他的一生跨越晚清、民国与新中国初期,以“教观双宏”的修证、“悲智双运”的弘法,以及“爱国护教”的情怀,成为中国佛教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代表,法师幼年聪颖,五岁启蒙,读书过目不忘,十八岁时,因父病逝,感悟人生无常,遂于福州鼓山涌泉寺出家,礼兴公开律师为师,法名“圆瑛”,字“悟胜”,次年,依妙莲和尚受具足戒,正式成为一名比丘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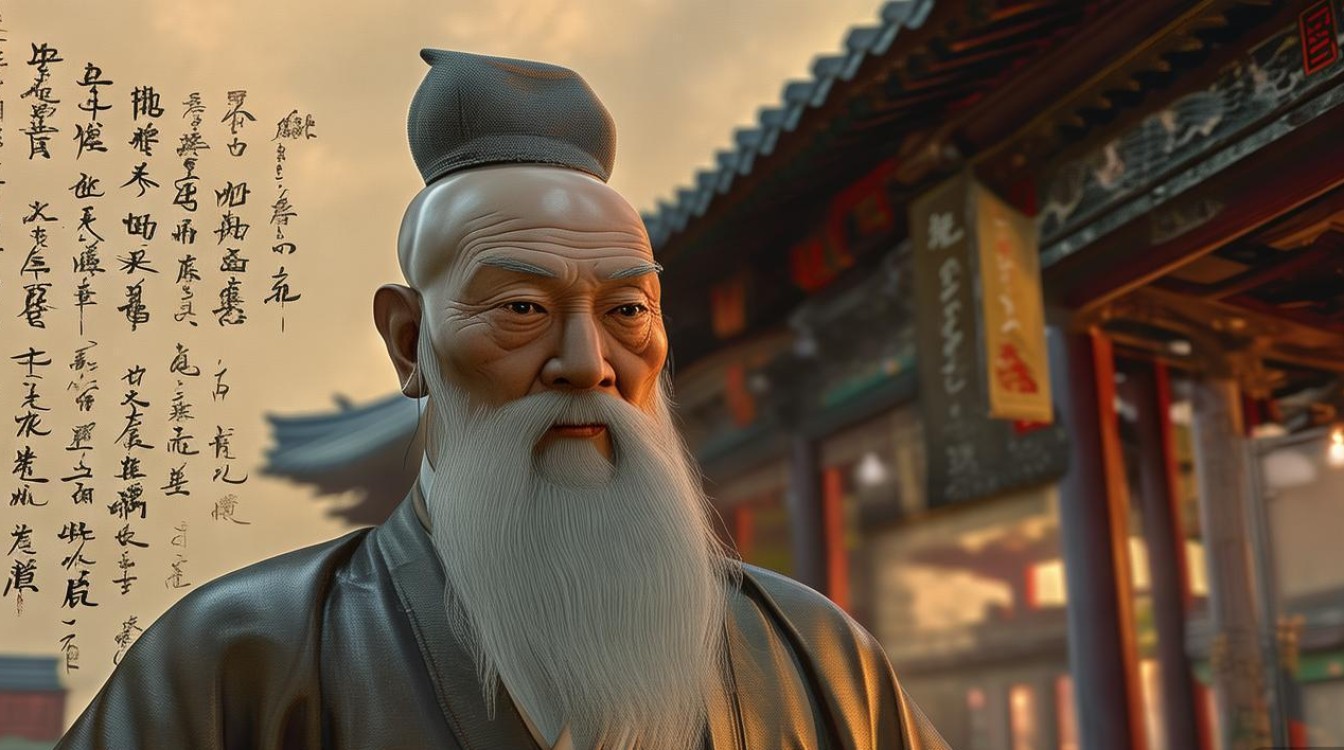
出家后的圆瑛法师,并未止步于传统僧人的修行路径,而是以“深入经藏,智慧如海”为志向,四处参学问道,他先后参访天童寺寄禅和尚(八指头陀)、宁波观宗寺谛闲法师、常州天宁寺冶开禅师等高僧大德,既研习禅宗明心见性的心法,又精研天台教观“止观双运”的体系,更对《楞严经》情有独钟,穷尽毕生心力注释弘扬,后世誉之为“楞严独步”,他在修行中强调“教观并行”,认为教理(经教义理)是修行的基础,观行(禅观实践)是证悟的关键,二者如鸟之双翼、车之两轮,缺一不可,这一理念不仅贯穿于他的个人修证,也成为他弘法利生的核心思想。
圆瑛法师的弘法事业,始于二十世纪初,他先后住持宁波天童寺、福州雪峰崇圣寺、宁波七塔寺、上海圆明讲堂等名刹,每到一处,皆以讲经说法、培育僧才为己任,1929年,他联合全国佛教界人士在上海成立“中国佛教会”,被推举为首任会长,此后连任多届,致力于整理僧伽制度、保护佛教权益、推动佛教教育,他创办“福建闽南佛学院”“宁波七塔寺佛学院”等院校,培养太虚、印顺等一批佛教人才,为现代佛教教育奠定了基础,法师还积极从事国际佛教交流,1925年应邀出席在日本召开的“东亚佛教大会”,发表《佛学之宇宙观》演讲,以深厚的佛学造诣赢得国际赞誉;1933年,率团赴印度、锡兰(今斯里兰卡)朝礼圣迹,促进中外佛教文化的沟通。
抗日战争爆发后,圆瑛法师以“国家兴亡,匹夫有责”的担当,挺身而出,组织“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”,自任团长,率领僧侣医护人员奔赴上海、南京、武汉等前线,抢救伤员、赈济难民,他曾说:“佛子报国,当不后人!”1937年,上海沦陷,法师因拒绝与日军合作,被逮捕入狱,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,他大义凛然,写下“我佛慈悲,不忍众生受苦;为国捐躯,在所不辞”的誓言,后被营救出狱,出狱后,他继续在后方弘法,号召佛教界“护国护教”,将讲经所得全部捐献给抗战前线,展现了“上求佛道,下化众生”的大乘菩萨精神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圆瑛法师拥护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,1953年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首任会长,致力于团结全国佛教徒、传承佛教文化,同年,圆寂于宁波天童寺,世寿七十六岁,僧腊五十九载,其著作《大佛顶首楞严经讲义》《圆瑛法师讲演录》等,至今仍是佛学研究的经典,影响深远。
圆瑛法师生平大事记
| 时间 | 事件概要 |
|---|---|
| 1878年 | 出生于福建古田县,幼年读私塾,聪颖过人。 |
| 1896年 | 于福州鼓山涌泉寺出家,法名圆瑛,师从兴公开律师。 |
| 1897年 | 依妙莲和尚受具足戒,开始参学问道。 |
| 1908年 | 于宁波天童寺寄禅和尚座下参禅,兼习天台教观。 |
| 1914年 | 开始在上海、宁波等地讲经,以《楞严经》为核心,奠定“楞严独步”地位。 |
| 1925年 | 出席日本东亚佛教大会,发表演讲,推动国际佛教交流。 |
| 1929年 | 创办中国佛教会,任首任会长,致力于佛教教育与僧伽改革。 |
| 1937年 | 抗战爆发,组织佛教救护团,因拒绝与日军合作被捕,坚贞不屈,后获释。 |
| 1949年 | 新中国成立后,拥护宗教政策,参与筹备中国佛教协会。 |
| 1953年 | 当选中国佛教协会首任会长,同年圆寂于宁波天童寺,世寿七十六岁。 |
相关问答FAQs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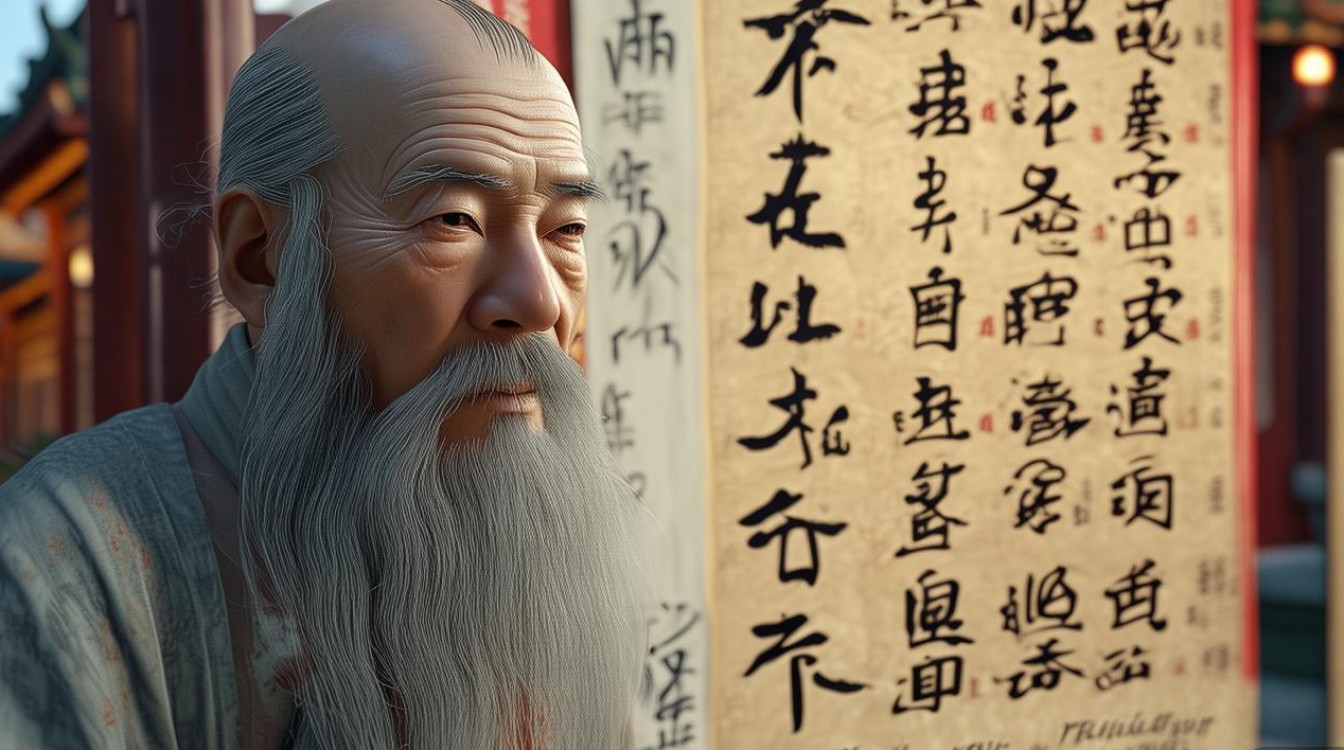
Q1:圆瑛法师的“教观双宏”思想具体指什么?对后世有何影响?
A1:“教观双宏”是圆瑛法师佛学思想的核心。“教”指教理,即佛陀所说的经教义理,如《法华经》《楞严经》等,是修行的理论指导;“观”指观行,即通过禅观实践体悟真理,如天台宗的“止观双运”,法师认为,若只重教理而不修观行,则如“说食数宝”,无法证悟;若只修观行而不明教理,则如“盲人摸象”,易入歧途,他一生倡导“教观并行”,既精研义理,注重经教阐释,又强调实修,主张“解行并进”,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:推动了佛教教育的系统化,使佛学义理得以准确传承;促进了修行与理论的结合,避免了佛教流于空谈或盲修的弊端,为现代佛教的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。
Q2:圆瑛法师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哪些具体贡献?体现了他怎样的精神品格?
A2:抗日战争期间,圆瑛法师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:一是组织“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”,自任团长,率领数百名僧侣医护人员奔赴上海、南京、武汉等地前线,设立救护站、野战医院,抢救伤员数万人,并募集物资赈济难民;二是以佛教领袖身份发表宣言,号召全国佛教徒“护国护教”,将弘法所得全部捐献前线,鼓舞了军民士气;三是面对日军的威逼利诱,坚贞不屈,拒绝担任“中日佛教会”会长,被逮捕后仍坚持“我佛慈悲,不忍众生受苦”的信念,展现了“威武不能屈”的民族气节,这些贡献体现了他“上求佛道,下化众生”的大乘菩萨精神,以及“国家兴亡,匹夫有责”的爱国情怀,将佛教的慈悲济世与民族大义完美结合,成为近代佛教界爱国护教的典范。